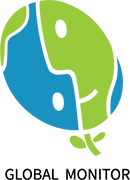戴安•菲利(Dianne Feeley)是底特律的退休汽車工人,也是〈汽車工人巡回宣傳網絡〉(Auto Workers Caravan)的活動份子。她2009年八月接受了勞工世界的訪問。
你怎樣評估這次重組計劃?一般的工會會員對這計劃和工會的讓步有何反應?假如他們之間有意見分歧,爭議的是甚麼?
汽車工人當然對管理層提出的重組計劃沒有信心!這個重組計劃是以犧牲我們的利益為出發點,而且是由一班決定生產越野車及貨車而不是高效省油車的管理層負責執行! 通用曾在90 年代生產電動汽車,但只是出產了幾百部。這事曾被拍攝為紀錄片 “是誰扼殺了電動汽車?”
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Chrysler)(所謂的 “三大”)出產的每一部貨車及越野車的純利是$10,000美元。它們專注於生產這類型車輛,把大部份小型及中型車輛生產轉移到海外或美國的外資廠房是一個深思熟慮的選擇。
通用和克萊斯勒的重組計劃揭示了更多的裁員和廠房關閉。2009年初,通用擁有62,400生產及技術工人(他們都是工會會員,有別於非工會員工的工程師和管理人員)。及至2014,通用汽車只計劃保留46,400名美國本土工人。 加拿大通用汽車在2005年有20,000個勞動職位,明年也會精簡人手至7,000.)
自30年前的汽車業危機起,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在“三大”車廠的會員已大降80%。1978年的時候,通用汽車有466,000工人,福特有192,000人,而克萊斯勒則有 97,000人,總計有755,000工人。而現在,通用才62,400人,福特有47,000,克萊斯勒只有14,000人。
我們從沒有從1979-83年汽車業危機其間所作出的讓步恢復過來。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還越來越支持這個理念:就是我們的命運是和汽車公司的福祉緊扣在一起的。每當環保人士提交有關提高排放標準的議案到國會時,不但只“三大”反對,我們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也挺身而出反對,甚至動員我們的會員參與寫信及遊行示威活動。
汽車公司在79年危機後的重組採用了 “精簡生產”的模式,不時反覆檢討生產工序,重複合併及淘汰職位。基於這個思路,他們引入“團隊概念”,即是管理層每星期,或每兩星期與時員工討論提升工作效率的方法。這加重了工作壓力。以往生產線工人只需每分鐘工作45秒,現在則要 “57”秒。這種“壓力型管理” 增加了前線工人的工作壓力,工人為了趕上節奏不得不加快工作步伐,結果導致更多工傷。
由於外資車廠在美國生產的車輛逐漸蠶食“三大”的市場佔有率,面對這場日益激烈的競爭,通用汽車和福特決定把零件部門賣掉,例如通用汽車的零件部門被分拆為美國輪軸(AAM)及特爾非 (Delphi),福特的零件部門則變身為Visteon。這安排不但大幅減少兩間公司的僱員數目,而且更為公司減省了相關的開支(醫療保險及退休金福利)。
受惠於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激勵措施,這三間公司還繼續在北美市場內興建廠房,可是,隨著供應鍊在全球的擴張,他們只有轉移到勞工較廉宜的地區建設。全球車廠每年的產能可達9,400萬輛,比他們的銷售能力至少多出1/3。
資方利用產能過剩來分化各個廠房的工人,無論廠房是在同一國家的同一地區或者是在地球的另一邊。只要有過剩產能,每當在新舊產品交替的時候,汽車公司便可藉此要求工人作出妥協。
這種讓步的邏輯和企業精英削減工人福利的方法,早在30年前便已出現。
或許在此應該解釋一下,有別於其它工業國家,美國工人享有極少的社會福利。我們沒有全國性的醫療保險;我們只擁有一個有限度及政府營辦的社會保障作為職業退休。自二次大戰之後,參加工會的工人曾代表多於1/3的全國勞動力,他們也曾成功向僱主爭取醫療保險及退休金。但自1970年,僱主以極度高壓手段導致工會會員急劇下降。今天,只有10%或以下的私人企業工人屬於工會組織。在工會沒落,缺乏社會保障和低工資職位急升的情況下,那些還有保障的工人唯有依賴現有的雇主才能保存福利。他們一旦離開工作崗位,便立即失去所有的福利。換句話說,那些高收入的工人只是低工資工作的滄海一栗。
同時,媒體和政客盡最大努力說服低工資的工人:他們的敵人是工會。由於這種不斷的反工會宣傳,對那些有多一點就業保障和福利的工人的政治不滿是相當大的。
有著這樣的歷史,我們更能夠理解為什麼在汽車行業裡高工資、參加工會的工人會感到害怕,因為他們見證了三大巨頭的職位消失。他們對工會能帶領他們對抗雇主沒有多大信心,他們不認為會獲得很多公眾的同情。由於工會會議從不討論策略,在面對經濟危機時, 他們也就不慣於自己思考如何改變這種狀況。
客觀地來看, 汽車工人面臨三重危機:普遍的經濟危機,汽車行業的危機及環境帶來的危機。
至於一般工人所討論的策略,也許大多數人也支持“購買美國貨”的觀點。當我問,“但什麼是在美國製造?”他們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畢竟,外資車廠使用的美國汽車零件,其實比美國三大巨頭的車廠還要多。同時,通用汽車在加拿大、墨西哥或中國製造的產品,是否該算是“美國的”的呢?大部分汽車工人都認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其他貿易協定也是損害他們的利益,認為這些協定應該被取締。但他們不明白,這些協定也損害其他國家的工人。
最近,我們的〈汽車工人巡回宣傳網絡〉與工人團體到了環保組織山岳俱樂部(Sierra Club)開會,討論車廠轉產這個主意。我們會見墨西哥瓦哈卡的農民,他解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如何傷害農民,迫使許多人放棄自己的田地,而轉到城市工作,特別是在美國和加拿大。我們能從其他國家的工人和農民的觀點獲悉自由貿易協定所產生的傷害,這可謂是第一手解說,也證明不只是我們自己國家的工人,而是我們所有人都受到傷害,僅僅是商家得益。
我認為,那種相信“購買美國貨” 就能解決問題的思想,將繼續主導美國工人。但我不認為會像80年代初那麼壞,當時汽車工人聯會鼓動種族主義,鼓勵工人粉碎外國汽車和蔑視日本工人。現在我認為,工人因美國公司紛紛往國外尋找最便宜的勞動力而感到泄氣。汽車工人不理解為什麼企業精英缺乏應有的愛國情操。然而,這是一種反動的反應,因為它不講我們需要的那種工人團結一致的立場。
我們試圖擴闊空間,通過〈汽車工人巡回宣傳網絡〉促進大家思考,尋找集體解決辦法。要知道,除了五六個美國城市(紐約,波士頓,芝加哥,舊金山灣區和芝加哥)之外,其他城市很少有公共交通和火車。一百年前,我們比今天擁有更好的穿梭城市的交通工具。然後,通用汽車在全國城市遊說成功,拆除了所有有軌電車,以巴士取代,而通用汽車則生產這些巴士。再到後來,連巴士都消聲匿跡(因為都用私人汽車代替了---譯按)。
20世紀的大部分公共工程圍繞政府資助的道路及郊區發展。我們現在變成了以汽車為中心的社會,但這是不可持續的。讓我們利用這個機會,把車廠重組和轉產,重新裝備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汽車工人巡回宣傳網絡〉要求車廠轉型,為輕鐵,巴士和高速鐵路系統重建基礎設施。面對重重危機,汽車廠可以轉型生產別的有用東西,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停止汽車生產,改為生產軍備一樣。當時車廠轉產僅花8個月就完成設備改裝。如果我們在經濟危機開始便轉產,現在我們可能已製造出燃油效率高的巴士。
政府現在擁有百分之六十的新通用汽車。左翼工會會員鼓吹以公有制形式, 由工人來管理瀕臨破產的汽車廠。一般工會會員怎樣看?
由於政府在救助汽車公司的同時,卻逼迫工會讓步,導致工人對政府會實行有利工人的方案沒有信心。但每當我們有機會同工人談車廠轉產,他們的反應都是,對,為甚麼不這樣幹呢?可見大家都覺得這是最合情合理的事情!公司精英當然不願意進行如此大膽和創新的計劃。事實上,三大巨頭依然想把製造盈利高的汽車留在美國,而把小型而省油的汽車拿到墨西哥生產(那邊的汽車工人每小時只有3.50美元工資)。
汽車工人仍然對業界過去一年所發生的事情感到震驚。他們也對奧巴馬要求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重組感到意外,不明白為甚麼政府要工人和經銷商負起全部責任,還要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把重組計劃修訂,直到把工資下調到同外資車廠看齊為止。今年7月份財政部更要求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的退休員工取消視力及牙科保健。
大多數汽車工人認為汽車行業應得到救助,也得悉政客如何企圖醜化汽車工人, 如聲稱他們懶惰和取得過高工資。
當我向工人提出應該由工人(包括生產工人,技工,辦公室職員及工程師)經營轉產的車廠,同時又在經營上吸納環境及社區積極分子的意見,大家都覺得合理。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這只是一個主意。
對於汽車工人聯會與公司之間的協議,工會會員與非工會會員的態度是否有很大差異?
過去,工人階級相信高薪工人能夠為其他不論屬於工會與否的工人,定下較高的標準。然而,過去30年來參加工會的工人比例減少,同時低工資的工作卻增加了。汽車零件業過去九成工人都加入工會,部份工人比之汽車三巨頭的工人收入也只略低幾個美仙而已。但如今汽車零件業的工人九成不屬工會,而且工資福利都降低很多。
受到媒體和政客影響,許多低薪工人不滿高薪工人。他們說:“我們努力工作,還要負擔自己的醫療保險;為什麼他們有養老金,而我們沒有?”
我覺得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和其他工會的狹隘,促成企業精英和政客有能力影響工人之間的團結。工會應該代表整個工人階級廣泛的權益,而不僅僅是自己的會員。如果我們不能團結,我們根本不能真正保衛自己!
最初,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爭取國家保健和養老金,但汽車三巨頭決定向工人提供私企褔利。如此一來,工人就得依仗企業才有福利。有一段時期,汽車三巨頭為近三成的勞動力提供了保健和養老金。如今醫療費用急劇上升,因此過去十年僱用合約中最具爭議的,就是保健,而企業亦要求工人分擔越來越高的保費。當然,低薪工人享有醫療保險的可能性很低。美國有近5千萬人沒有醫療保險。
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的工人,特別是鋼鐵工人較為團結。他們在全國各地組織一連串集會,堅決支持單一由政府支付的醫療保險制度。
有無比較大膽抗爭,來捍衛他們的工作和工資的車廠工人?
讓我舉四個例子:
1. 紐約州雪城的New Process Gear零件公司曾經是克萊斯勒的工廠,但現在已經由加拿大的一個重要零部件供應商馬格納(Magna)擁有。當馬格納收購該工廠時,有4000名員工,目前則是1000人。在過去的幾年合同,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當地支會接納了一系列的讓步,包括把清潔工作讓給非工會的公司,降低工資,以避免該公司的倒閉。支會接受了不罷工的條約,甚至不能夠因醫療和職業安全罷工,連組織僅為宣傳而設的糾察隊都不行。
最近,該公司重回談判桌,要求進一步削減工資;工人投了反對票。他們知道一旦拒絕新約,公司有可能會關閉,但工人已經受夠了,並且違背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的立場,三度否決新合約。該工廠將於2011年或2012年關閉。
2. 去年全美只有15次罷工(以每次超過1000名工人參與來計算)。有一次罷工是發生在通用汽車90年代中期出售的一級零件供應商美國輪軸製造(AAM)。該公司是有盈利的,汽車工人聯會的領導認為基層工人,不應該和汽車三巨頭的工人一樣接受讓步。然而,公司總裁要人讓步。他採取兩個策略:以墨西哥廠房為通用汽車供應最低數量的車軸,並且獲得通用汽車支付罷工期間的運費;同時調動低一級的管理人員生產車軸,以履行豐田的合約。通用汽車開啟和關閉不同的組裝廠房,以調配有限的車軸,但是這策略讓美國輪軸和通用汽車可以迫使工會接受恐怖的合約。
汽車工人聯會同意這次罷工,但事先沒與墨西哥工會取得緊密聯繫,使工會罷工變得鬆散。此外,工會幹事不讓罷工工人阻止貨車與其他人員出入工廠。假使工會真的阻止他人破壞罷工,的確需要大規模的公民抗命和社會支持,但是這并非不可能。
汽車配件商美國輪軸工人經過87天的罷工(比1937年工會的靜坐罷工還長一倍。那次行動迫使通用達成協議),決定減低工人的損失並接受減薪安排協議。不少工人選擇給公司「買斷」合約。
3. 一般而言,克萊斯勒車廠工人都奮力抗爭,拒絕讓步。部分原因是克萊斯勒有一較為獨立的領導層。另外,克萊斯勒工人正要面對部分工廠關閉。地方分會領導曾舉行示威、游說地區與全國的政客及組織車隊的方法反對關閉車廠。
4. 由於福特亦計劃取得政府的緊急財政援助,福特與汽車工人聯會正開始討論重開協議,但當地工會幹事則反對太大讓步。他們明白需要迫使福特降低要價,才能令工人接受。未來數月雙方將持續角力。
一般認為三大汽車廠的失敗主因是高薪削弱競爭力, 使其敗於豐田汽車等日本車廠之下。」據報,日本設於美國的車廠平均勞工成本是1小時25美元,而三大汽車廠平均勞工成本是日本的兩倍。日本設於美國的車廠與三大汽車廠的工資是否真的有這麼大差距? 這差距是否導致三大汽車廠的失敗的主因?削減工資與福利又能否改變三大汽車廠的命運?
日本設於美國的車廠與三大汽車廠的工資幾乎是一樣的。事實上,至少有一家豐田的美國汽車廠的工資較三大汽車廠為高。無論如何,工資佔製造汽車的開支約百分之八至十。不過,日本設於美國的車廠只有約25年歷史,退休員工亦少於1000人,但三大汽車廠的退休員工已超過百萬人。當三大汽車廠討論工資時,他們會把退休員工的福利與現職員工的工資及福利混為一談。三大汽車廠所計算的天價『工資』為每小時70至73美元,但這其實是把『勞工成本』當作工資。而這『勞工成本』還包括車廠聘任員工的其他成本如福利及各種稅款。現在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同意接受最新的兩層工資協議,新聘請的員工工資每小時14美元及沒有退休金。員工亦需分擔醫療保險的費用。
從條例上來說,退休金與現職員工的工資是分開帳戶的,但管理層卻把退休金的成本計入現職員工的工資成本中。
在保健方面,早前的協議已把員工調高的生活費用作支付醫療保險的福利。因此,車廠並沒負擔所有的醫療保險成本。
美國的醫療保險費用已持續上升,但我們的保健質量卻沒有相對提升。現在我們的保健制度既無效率又以利潤掛帥,實是需要解散。我們需要的是如其他工業國家那般適用於全國人民並獨立於僱主的保健制度。
諷刺的是,通用汽車對於能夠在加拿大製的車輛上節省1500美元而感到自豪,但他們卻不支持把改變現時的保健制度,改為由政府單獨出資的方案,雖然這有助減輕車廠的負擔。
再看汽車工業的生產力,它每年的增幅都不少於3%。而在過去30年,汽車員工工資及福利的增幅卻總是少於生產力的增幅。美國勞工事務主管機關公佈2009年第二季(4月至6月)整體經濟的生產力增加6.4%,同時每位工人的工資卻減少5.8%。
企業精英力爭為自己取得更多利益。華爾街日報在分析2007年的工資數據後,指出高層的工資佔工資總額三分之一。這支出並不包括購股權及其他福利,這支出安排明顯向高層傾斜。我們的社會愈見不公平。
美國工人對日本人或亞洲人有沒有民族主義情緒?
八十年代初期對美國工人對日本人的確有極其民族主義態度,而汽車工人聯會也鼓勵工人破壞豐田汽車。1982年更有一個華人因為被誤以為日本人而被打死。
我不認為今天美國工人對華人和墨西哥人還有那程度的憤恨,部分原因是大家知道那些工人賺取微薄薪水,他們也知道,是美國企業自己把工作外判給墨西哥和中國工廠。
今天在底特律的情況是怎麼樣?該城市的經濟不景已十年,高失業率及市民遷徙等等。汽車業重組會否給該市的工人和居民另一個打擊?是否有任何積極抗爭的跡象?
與大部份城市一樣,底特律的不景超過十年。工業外移,然後較高收入的工人中產階層也外移。
今天底特律在種族分隔上是最嚴重的城市。85%是非裔美國人,其餘是墨裔美國人、原住民、阿拉伯裔美國人及白人。人口最高曾達二百二十萬,今天維持於大概九十萬。底特律有40%房屋是荒廢的。
市內已沒有百貨公司,及只有幾間電影院。雖然剛宣佈有一家全國性的雜貨連鎖店會在明年在市區外圍開業,但目前為止尚未有一所。
官方的失業率高企於22%,即大概每三個工人中就有一個是失業的。底特律已建有一個廣泛的供水系統,但有三萬人沒有自來水供應。雖然90%的工作階層擁有自己的房屋,然而今天很多人無能力負擔修葺破爛的前院臺階或在房屋表面髹上油漆。當他們荒廢了該房屋,賊人便拿走發熱器和偷取所有有價值的東西包括銅線, 此舉令鄰舍毀壞。
我們也至少有兩萬人無家可歸,許多越戰退伍軍人。但我們的城市擁有大量住房,任何人都不應無家可歸!
與此同時,底特律仍然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文化中心,充滿了爵士、怨曲、西部田園、世界音樂、古典、福音、搖滾和重金屬等。它有詩人和有以傳道人,學生和工人身份的語言藝術家。許多藝術家因為它的文化多樣化和相宜租金而選擇在底特律居住。
儘管底特律是一個汽車城,三分之一的居民沒有汽車。一世紀前的集體運輸系統較之今日還好。很多城市都能有效率地把人們從機場送到市區。但底特律不行。我們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是需時兩小時三十分鐘車程到市中心的公車。
受到政客和媒體的鼓動,最普遍的觀點是認為問題在於“全球化”。我覺得工會幹事鼓吹的是一種面對全球化現象的無助感。前頭提及過,大多數工人以“買美國貨”作為唯一可行的策略。但這是他們以自己的角度反對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據中國財訊網的報導,2009年上半年,中國汽車銷量已經達到六百萬輛,意味著中國已過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市場。中國在短時間之內成為汽車製造業的重要國家。儘管全球汽車業面臨危機,德國MAN公司決定以百份之二十五股權成為中國重汽集團的策略伙伴。這似乎顯示西方汽車製造業巨子對中國汽車業和市場的信心。但中國汽車工人月薪只有人民幣二至三千(美元二百九十三至四百三十九元),這對西方和日本汽車業工人有什麼影響?
中美兩國汽車業市場龎大,而由於中國工人薪酬較之美國工人相差甚遠,汽車商都有意在中國增產。不過,美國的市場遠離中國,運輸成本變得不明確。我相信汽車業三大巨頭會以墨西哥而不是中國作為他們生產小型汽車的基地。墨西哥工人時薪3.75美元(月薪美元六百元),褔利不多; 而且在墨西哥製造的汽車可以在一個星期內運送到美國任何一個角落。
克萊斯勒以5.7億美元投資在墨西哥薩爾蒂約新的引擎制造廠房。2008年福特汽車宣布在墨西哥三個廠房投資三十億美元。事實上,福特三分之一的北美汽車是在墨西哥製造。通用汽車在墨西哥擁有比其他同行較完整的零件生產線,同時三大巨頭都在墨西哥擴張他們的供應鏈。
我個人懷疑通用汽車,褔特和克萊斯勒已不打算在美國生產汽車。他們把生產線外判到墨西哥以及部份到中國。2007年三大巨頭在本土制造的汽車,只占49.2%;2008年再稍為下跌到47.5%。同時外資車廠年產約三百三十萬輛。
根據一些報導,三大車廠的工人享受很好待遇,因而成為「工人貴族」或「中產階級」,不能發展出階級意識,來獨立行動及堅決地捍衛自己的權利,更不用說促進激進的社會變革。你如何評價這種觀點呢?
我相信所有美國人,甚至那些沒有能力去消費的,皆生活在一個「消費社會」中。這是我們大眾文化的一部分。記得911事件後,布什總統呼籲人民做什麼:是買東西!(所以追求高消費不光是工人的責任)
雖然美國有過重大的社會改革運動,但現在大家都堪稱是「全球化時代」之前才有的東西。同時,三十年來,所有總統都在極力促成我們的無力感:我們無法阻止里根總統在1981年解雇罷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員,我們無法阻止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我們無法阻止伊拉克戰爭,我們不能阻止嚴重削減市政服務等。許多年輕人也消極接受右翼宣傳,相信當他們年老時,社會保障養老金將不復存在。
誠然,工人不會獨立思考。但是,我們曾在哪些地方被鼓勵思考呢?在學校裡,我們被教導認為「美國模式」只可有兩個政黨;美國不像加拿大的模式或歐洲的模式,我們用不著他們那種議會及多黨制,用不著他們那些社會主義的黨。
工人階級的組織在哪裡?在工會仍然存在的情況下,它們是糾纏於兩黨制中。民主黨及共和黨之間是有分歧的,但企業精英對兩黨皆支持。在上次選舉中,大多數企業是支持民主黨的;據估計他們花了至少五百億美元,而他們花掉那麼多錢,會得到什麼?美國國會難道會通過有政府負全責的醫療保險計劃?這樣的方案,連提出來也沒有。為什麼?即使工會同樣花了大量的金錢和時間支持奧巴馬和民主黨,但企業老板花上更多(所以工會還是無法影響政府)。
即使在工會會議上,普通工人是不會被鼓勵去討論策略的。相反,他們只要放手讓工會幹部為大家談判,並在必要時「支持他們」,就夠了。但是在汽車工人聯會成立之初,會員都富抗爭精神。在1936年,通用汽車工人靜坐罷工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當時的社會主義黨發揮作用,帶頭抗爭。但它的歷史現在好像都被遺忘了。
我們認為,既然聯邦政府現在「擁有」通用汽車及克萊斯勒汽車公司,那就應該把工廠轉產,生產集體運輸設備及應用綠色技術。聯邦政府,他們本應以我們的利益為依歸,但他們卻反而要通用及克萊斯勒關閉更多工廠,解雇更多工人,更將我們的工資與非工會工人掛鉤。我們〈汽車工人巡回宣傳網絡〉的目的就是指出,爭取集體的解決方案是可能的,而求救於個人的解決辦法是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