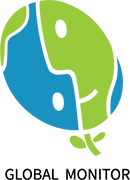作者:梁柏能(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主席、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研究生)
紮鐵工潮擴大,再次提醒我們要正視香港勞資衝突加劇這個「深層矛盾」。香港勞資協商機制失效,是這次工潮擴大的重要原因。香港市民享有「勞動基本權」中的「工會組織權」和「罷工權」,但法定「集體談判權」則於1997年被臨時立法會剝奪。
沒有法定「集體談判權」,工會原則上仍然可以代表員工與僱主或商會進行集體談判,然而現實上這種談判有很大局限。其一是僱主或商會一般不願意承認工會的代表性,拒絕與之談判,遑論訂立集體協議;其二是即使雙方訂立協議,協議的執行也不能得到具體法律保障。
集體談判難以進行,員工就只能和僱主就薪酬和福利進行個別談判。在香港,只有少數行業有制訂行業性工資,如教師和公務員。這些行業,通常有較龐大的 工會或專業團體組織力量,以及較統一的僱主。但大部分行業,員工都只能和僱主單對單談判薪酬和福利。在勞資勢力懸殊的大環境下,僱主通常採取分而治之的策 略,員工的集體利益難以得到保障。再者,香港現時自由放任的經濟制度,難以杜絕商人聯手向工人壓價。員工缺乏集體議價能力,正是香港貧富懸殊惡化的成因之一。
要緩解香港勞資失調這個「深層矛盾」,立法保障「集體談判權」起理順勞資關係的作用:
1. 確立規範有序的勞資協商機制,避免勞資衝突失控
欠缺規範有序的勞資協商機制,員工在面對不合理的工作條件或要求時,反應容易走向極端。員工一方面只能啞忍,面對巨大物質和精神壓力,久而久之容易 形成種種社會悲劇;另一方面,忍無可忍時,工人的不滿又會出現瓶頸式總爆發。依據歷史和其他國家的經驗,這種爆發容易訴諸暴力,甚至破壞社會秩序,抗爭者 的要求亦難有協商和迴旋空間。賦予工會組織「集體談判權」,讓員工成立有實質代表性的工會,可以引導僱主和員工透過定期和制度化的協商,疏解勞資糾紛和矛 盾,也可以促使僱主和員工全局性的考慮問題。即使出現工業行動,衝突失控的機會亦會減低。
2. 以「集體談判權」彌補《僱傭條例》的不足
《僱傭條例》亦是勞工標準的集體約定,是法律要求的最低勞工標準。勞工標準立法的目的,當然不是期望員工權益的保障只停留在最低水平。透過有法律保 障的集體談判,可以對員工利益作出高於法定標準的集體約定。此外,《僱傭條例》的規定,很大程度上是原則性的,不同行業和企業有其特殊的勞資關係。若能建 立有效和合理的集體談判制度,個別保護性的勞工標準的立法,可以相對地減少;對個別行業或企業勞工標準的約定,也可以更具適切性。
3. 符合國際條約要求
「集體談判權」是聯合國《國際勞工公約》所確定的核心勞工權利。港府早已確認的第98號《關於適用組織權和集體交涉權原則的公約》第4章第4條規 定:「在需要時,應採取適合國家條件的措施,鼓勵和推動僱主或僱主組織同工人組織之間,充分發展和利用集體協議的自願談判程序,以便通過這種方式確定就業條款和條件。」現階段港府正是時候立法保障「集體談判權」,履行國際條約所規定的責任。
4. 香港勞工標準應與已發展國家看齊
絕大部分歐、美、日等已發展國家都已就「集體談判權」立法。即使在東亞地區,經濟實力與香港相當的新加坡、台灣和南韓,對此同樣有法例保障;就連工 人權益常遭詬病的中國大陸,也訂立《勞動合同法》落實工人簽訂「集體合同」的權利。可見,「集體談判權」是各國調節勞資利益分配的根本制度性保障。港府再 不爭取時間立法,長期落後於國際形勢,難免招來「官商勾結」和「資本壟斷」的指摘。長此下去,不單有損社會和諧,更不利長遠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