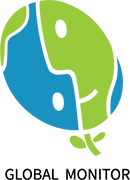以剝削的遣散費 為製衣時代作結
黃玉蓮
編按:當成衣工人的經歷堪成香港七八十年代集體回憶的重要部分,我們的媽媽、鄰居的兒子,甚或自己,都曾經是成衣工人。進一步出版之《千針萬線——香港成衣工人口述史》,從工人們的故事固然得以側見一個工業以至一個城市的經濟興衰史;並透現工人們自身的尊嚴,以及她╱他們當時和僱主的「道德關係」和後來全球化時期這段關係的崩潰。本篇會是毛衣廠葉大姐的故事。
訪問╱黃玉蓮、王曉 撰文╱黃玉蓮
葉大姐:照燈的日子
葉大姐,1945 年出生,訪問時58 歲,福建石獅人。家裏九兄弟姊妹,排行最大,由於家貧及孩子太多,父母便把葉大姐及兩個妹妹送給阿姨撫養。
阿姨在刺繡廠工作,工廠就在家隔壁,葉大姐每天去看他們工作, 15 歲時決定入行,初入行時做編花,結婚後當上「輔導員」,教人繡花和串珠。
1981 年,她帶着大女及兒子來港,期望與多年沒有音信的丈夫重聚。但到港當日,只有奶奶接車,並說只會帶一對子女回家,不歡迎葉大姐;因為葉大姐的丈夫跟其母親說過,若她把葉大姐接回家,他便不認她為母親。
在人生路不熟的處境下,葉大姐只好讓子女跟奶奶回家,自己則到丈夫的舅母家暫住。不久葉大姐在玩具廠覓得工作,便叫兒子來跟自己住,一起「捱啊捱啊捱」。就這樣,葉大姐展開了她在香港的工廠生涯,在1988 年轉到製衣廠,高峰時期月薪萬多元。
但過去5 年開工不足,在訪談前期間剛遭遣散,並正通過工會追討合理的遣散賠償。
我們訪問葉大姐時,她多次強調她是靠自己的雙手把兒女養大,說話中流露着莫大的自豪與成功感。
「我先生72 年來香港,他媽媽和弟弟在香港。我18 歲(1963 年)便結婚,19 歲生女。但我從72 年到現在也未見過我丈夫本人,所以我是靠我一雙手湊大我的仔女,從子女結婚至買樓也是我自己捱出來的。那時是政府讓我來香港找丈夫的,由我提出申請。」與 丈夫關係疏遠,葉大姐申請到香港時已作好心理準備,丈夫可能不會相認,因而寧願帶着大女及兒子到香港,把二女及細女留在鄉下。
「最初政府批准我的兒子和幼女跟我來港,我說若批准我來,我便要換。因為我不知來港後我丈夫要不要我。如果他不要我,我大女可以去做工,我們兩個工作便可 以養鄉下兩個女和兒子讀書。所以要換大女來。大女當時虛齡18 歲。政府考慮我的辛苦,就讓我細換大。」「價錢不錯」,只因密密手由80 年代至90 年代初,葉大姐辛勤工作,生活節儉,一心一意把子女養大。當時工廠訂單還充足,總是「工找人」,葉大姐因而從沒想過會有沒工作的日子。
「我在81 年先做玩具廠,之後我到一間叫『海城』2 的風扇廠做,做了3 年。」「當時製衣業興旺,人人也入製衣。於是自己就跟潮流,一起入製衣業。初時(87 年)做查衫和剪線頭,由人介紹,問我做不做照燈。我做冷衫,照燈就是查剛織出來的冷衫有沒有爛、花紋對不對、合不合格等。若有問題要給補衣織補,補完再拿去洗水。做完挑撞後,在生產線上我是第一個做檢查的人。
「88 年『大光明』製衣廠開張,那時要見工,他說是做照燈,6 月1 日開廠,我打電話去問,那便行了。
「這是我第一份在製衣廠的工作。由1988年6 月1 日做起。我把日子記得那麼清楚是因為那天是工廠的開廠日。工廠一開始,我便來這兒工作。是由人介紹入去做。他說在長沙灣的大光明請人,問我去不去。從前製 衣廠都多在(九龍)附近。」「大光明有以下的部門:第一是縫盤;第二是挑撞。縫完整件毛衣後,挑撞是要用小勾把線頭藏回毛衣內。縫盤由機器縫製,挑撞便用 人手。跟着便是由我照燈,然後洗水、燙部燙衫、車嘜頭(即牌子標誌)、查。第一次查衫後做補衣(初時衣服有問題便要補,然後洗水,如洗水後有問題, 查之後再補過),之後再查一次才包裝。
縫盤的人數會多些,有十多個。挑撞在開始時會多些人,旺場時十個八個。補衣有時有十多人。初時有些縫盤工作在大陸做,但技術不好,很多爛衣服,所以需要多 些補衫的人。但照燈就只有我一人,由我做所有的工作。」大光明廠生產的毛衣是蠻有名氣的名牌貨,運去澳洲、美國、日本,以往在太古城亦有出售,因此查貨特 別嚴格。既是名牌貨,自然售價不菲。但工人從中又得到多少工資呢?
「從前照燈的價錢都不錯,可以掙不少錢。其實各部門,各有千秋,熟練了便可多搵些錢,生手便不會快。」細聽之下,葉大姐所說的「價錢不錯」,是要求工人全日不停工作才可以達到的。
「我當時是計件數,每一個人的件工價錢也不同。老闆總會有一個價錢:每件衫算多少錢。我是計打,但要做好久。
我初入行照燈,一打才一元。初入去比較難照,一小時都可以做十多打。照熟之後,如果容易照的,一小時有廿幾三十打,但也好辛苦,如一件衫要看兩個袖,再轉 一圈,又要再揮兩次,一件衫要放上放下做5 次,12 件便要做60 次。所以也幾辛苦。坐着做,兩個燈照,照完大燈,之後照手袖的細燈。剛做時真是很累,工作一天後,肩膊好累。現在手指骨也會微曲。要有一個特定的姿勢,才 能把毛衣穿入照燈內,要不然怎放也放不下。有時手指也會痛。工作時燈着了,手會熱。到洗手間後洗手,水是冷的,一冷一熱,手部骨節漸漸變得酸痛。」燈着手 熱,洗手水冷儘管辛苦,仍然開心,亦不多計較。「最開心的時候是掙最多錢的時候!工作是很辛苦,但辛苦得來很開心。真的很辛苦,由早上8 時、9 時便上班,如果有工作做,我便要很早返工。8 時多便返,做到凌晨1 時2 時才回家,要不然怎能掙那麼多錢!中間放一個小時吃飯。晚上只有半小時吃飯,都是吃麵包。吃午飯時間一定要停工,廠的裝置是這樣的。但如果多工作,他們便 『隻眼開,隻眼閉』。但我也稍停一小時,養養精神,那便可以捱到凌晨,若『過度』疲勞便不能工作。那時長沙灣有通宵車,但貴些。
「以前我的貨疊得高高,比我還要高,我自己一個人在衣服堆中間,我笑說自己在『四川盆地』。我又看不到他們,就住在『四川盆地』。
「以前年初九開工便做到年三十也很旺,天天也有工作,全年都旺。開通宵班便由8月份開始,趕在聖誕節落貨,3 月至6 月也很忙。我們經常也有很多工作。不是旺季時,也要(晚上)8 時才下班。10 時也是常事……
「掙到最多的一個月有萬多元,那時是『四川盆地』的日子,那些貨真是很多……
91 到93 年也不錯,一年中只有幾個月較少貨。」在工廠仍不愁沒有訂單的90 年代初期,葉大姐從沒有想到會有沒工開的一天。「挑撞在我隔鄰,她們對我很好。她們說: 『葉大姐,我教你挑撞。』我說自己有工做便好了。當時沒有想到那麼長遠,想做到60 歲就好了。怎知道未到60 歲便失業。」葉大姐工作的製衣廠自1997 年開始搬回大陸東莞,初時還有訂單,原來一個月也有千多至二千多打的工作量。1998 年金融風暴之後,工作量大減,約在5 年前開始開工不足,但一年都有數萬元收入,最少也有4、5 萬。到2002 年便開始沒有工作,全年收入只得9000 多元。至2003 年,由葉大姐所負責的部門及往後各工序的部門全遭刪除,工人全被遣散。
「現在那間公司還在,還有縫盤和挑撞,只是由我的部門開始刪除,遣散我們。(其他部門)全遷返大陸。」在2005 年之前,由於香港擁有成衣配額,很多工廠老闆仍需在港設廠,才能保留他們的出口成衣配額。不過,80 年代隨着中國大陸的開放,不少工廠都漸漸北移,只留下部份工序在香港的工廠完成,以滿足獲得成衣配額的要求。葉大姐那間工廠更在1997 年金融風暴後,進一步減少仍留在香港的部門,以降低成本。老闆在遣散工人時更鑽法律漏洞,剝削工人。
一年20 元遣散費
「遣散有賠償。賠了我1200 元多,我做了15 年半,哪有這麼少?所以就想爭取。於是來工會找幫忙。
「想不到賠償得那麼少。如果照勞工法例,就不只這麼少。也不知他怎樣計算。
「工會沒有替我們計遣散費,但我們到勞工處,教我們自己計。用公司工計算,一小時25 元。一天工作8 小時,我一天便有200元。一年可計18 日,我做了15 年半,最後,公司即要賠55500 元。那天勞工處叫那經理來商討,他答應把遣散費增至4000 元。我做了將近16 年,即一年只有20 元?我拿他廿元有什麼用。
「廠長稱是我包頭。我不用找人來,總之我包了照燈部門來做,但我從來也沒有拿過加一,也沒拿過有薪假期。工具又是工廠的,我根本不用準備什麼。工廠如果堅 稱我是包頭,他們就不用賠償費用給我。但在勞工處有一條,如果我的生產工具是由工廠提供,又在工廠內工作,就不算是包頭。」回想當年晚晚加班的日子,葉大 姐從沒想到還沒到60 歲便因開工不足而失業。幸好兒女已成家立室,也各有工作,所居住的樓宇亦早已供滿。失業後她由兒子供養,自己省吃儉用,生活還算可以。就如她說: 「我當時最大希望是,勤力工作,可以買樓,把子女湊大,見到他們成家立室。現在全部任務已完成。(笑)全部子女都成家立室。」她一生自食其力,養大子女的 心願,總算是已經達到了。
(文章輯自《千針萬線——香港成衣工人口述史》,經刪節。另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