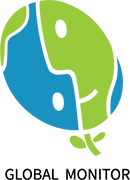2010年10月13日,天氣晴朗。我們從科隆出發,驅車前往位於萊茵河東岸的城鎮萊沃庫森(leverkusen)——世界著名的三大化工企業之一,也是德國三大產業支柱之一,醫藥化工巨頭拜耳集團總部所在地[1]。當地的主要產業就是汽車和醫藥化工。我們要拜訪的從事勞工服務的“相互作用”團體就在此地。幾位工人被邀來為我們介紹自己的境況。不過,這裡且從拜耳與環保談起吧。
拜耳的環保與污染備忘錄
先說說科隆。科隆是一座美麗的城市,高樓不多,住宅樓大抵在五六層以下,樣式和顏色搭配都很和諧美觀。家家戶戶的陽臺上總有鮮花,牆上常有藤蘿等攀援植物。自然與文明似乎融合無間,相得益彰。私家小汽車雖然和在中國城市裡一樣多得難以找到停車位,但也有越來越多支持環保的人士改以單車(即自行車)代步。水龍頭裡的自來水可以直接飲用。空氣是清新的,這樣的空氣在中國一般的大中城市裡已經享受不到了。這跟環保運動的興起以及污染工業的大量外移有關。一位來訪者說:以前看到歐洲城市的照片,以為只是攝影家或旅行者在少數漂亮地方選景拍攝的,來了才知道,原來這裡的景觀處處宜人,就連店鋪的招牌和廣告也頗有些品位,不像大陸那樣普遍帶著粗俗或暴發戶式的張揚。萊沃庫森也是如此:處處都是可以入畫的景致,不論是自然風光、住宅區、小公園還是臨街店面。如果你到拜耳的網頁上看看,會發現“環保”名列它的四大目標之首。拜耳在美國的分公司曾被美國化學理事會(ACC)授予2002年度大公司責任關懷領導獎,以表彰其對環境保護和安全生產所做出的傑出貢獻。再對照這裡的社區環境,興許你會忍不住伸出大拇指讚歎道:“這真是個恪守‘企業社會責任’、奉行‘可持續發展’的‘綠色標兵企業’啊!”
不過且慢……先聽聽知情的德國人士的介紹吧:
拜耳公司的前身是一家染料企業,1863年創辦于今天德國烏珀塔爾市的巴門(Barmen),1891年在萊沃庫森買地建廠,1912年將總部遷移到萊沃庫森。這裡早年是個漁村,拜耳公司建廠之後,才開始發展為小城鎮。初期擴建時,拜耳公司曾經在農民的土地施放毒物,污染了土地,當地農民沒法耕種務農,只好到拜耳的工廠上班。生產過程中,有毒廢料未經處理就棄置堆放在周邊,在這片土地上建房入住的人,有的因而中毒死去。至今城裡仍有部份土地沒有用來建房,因為地下埋著拜耳工廠的有毒廢料。遭殃的不只土壤,還有水源。為此,市政府只好把地下水抽到遠離萊茵河的地方,以防有化工原料污染過的地下水流入河裡。
經過如此這般的“原始積累”之後,大老闆是否“洗心革面,改邪歸正,回饋社會”了呢?不妨抄錄幾則消息,權且稱為“拜耳的環保備忘錄”吧:
1970年代,拜耳控股的位於墨西哥的某工廠造成了附近城鎮嚴重的鉻酸鹽污染。廢料被棄置在工廠四周;街上的坑洞用鉻塊任意填補。污染物還進入水源。結果,兒童開始身體酸痛,當地有人因此死亡,還有人因鉻中毒引起皮膚反應。後來該廠被墨西哥衛生部門關閉。包括員工和居民在內的受害者,還有一些肺癌的病例,無望得到賠償。[2]
1986年11月26日,拜耳公司的甲醇流入萊茵河,造成河水污染。
1997年5月,拜耳公司被美國環保署宣佈為最嚴重的污染者。
1993年,拜耳規劃在台中縣設廠,生產劇毒的甲苯二異氰酸酯(TDI),儘管臺灣政府給予大量優惠條件,但民眾和環保團體憂慮工廠排放光氣或其它有毒物質外泄的危險,群起杯葛,要訴諸公投。環保團體質疑拜耳生產TDI而非MDI(二苯基甲烷二異氰酸酯),是在轉移落後產業,因為發達國家正大力提倡以MDI替代高毒的TDI。儘管拜耳信誓旦旦保證工廠的環保與安全生產措施,但言猶在耳,德國本土的拜耳化工廠卻發生了一起二胺基甲笨外泄事件。1998年,拜耳被迫從臺灣撤資,轉而在美國、中國大陸設廠並大打環保牌,諸如舉辦“拜耳青年環境特使”活動云云。
……
拜耳現狀——外判·分流·裁員
在“相互作用”機構裡,最先為我們做介紹的是拜耳的工人X。
1976年X在拜耳公司上班時,員工總共有5萬名,現在老公司裡只剩下1萬人了。工廠主要從事醫藥和特殊材料的生產。從1995年開始,一些車間和產品陸續被賣掉。在拜耳公司原址上,目前已有了50家公司。原屬拜耳的化學工業如今已賣給一家叫“旺盛”的公司,有4千工人。該公司現已獨立上市,與拜耳脫離關係了。拜耳的其它一些工廠也都賣給別的公司。包括物流在內的所有後勤工作則外包給服務公司。拜耳曾有自己的印刷公司,後來負責印刷公司的老闆把公司接收了自己幹。能源部份單獨成立的公司有2000名員工,拜耳持有50%股份。拜耳在物流公司也有股份。還有原來由拜耳自己生產的產品也陸續分流給其他公司。
150年前,拜耳從事化工行業時,就是由染料起家的。由於生產成本昂貴,所以生產染料的公司被分離出來,單獨成立了這樣一個公司。現在這個公司裡勞資之間一直在鬥爭。“相互作用”的成立與這個鬥爭密切相關。
跟汽車行業相比,這裡的外籍人員比例較小,僅占5%(其中不包括來自東歐、東德的工人,因為他們很快拿到了德國籍)。
萊沃庫森這座城市共有16.2萬人口,其中1.8萬人(11%)為移民背景,大多數來自土耳其。但是早先,前南斯拉夫移民比例曾是最高的,達到25%,因為拜耳一直在東歐國家招工,此外是土耳其(占22%)、義大利、希臘、波蘭人。本市的失業率為10%(在全德國,有100萬沒有合法居留證件的打工者)。市內有個難民服務中心。至於他們這個機構,則沒有相關的統計資料來源。
土耳其裔工人L的介紹
L在拜耳屬下的德司達公司(DyStar)[3]幹了23年。2009年公司宣佈經營不善破產,他被解雇。一家新公司接收了德司達。接下來的10個月,全體員工拿原工資的80%,新公司聲稱會幫被解雇的工人找工作,還做了種種承諾,比如說公司的情況會好起來,工人可以回到工作崗位,等等。L選擇了呆在這個新公司,繼續工作和加班。儘管公司宣稱沒有清償能力而破產了,但加班從沒有停止。L現在承認,當時選擇呆在新公司是錯的。他後悔,當初本應該跟其他工友一道和新公司對簿公堂。3個月後,新公司召集這些留職的工人,說他們可以回廠工作,但不再是正式工,而是臨時工了;工資水準降低(L的工資比原先少250元),養老金等福利也都沒有。合同簽到年底,之後能否續約也是未知數。說到這裡,他再次表示,後悔沒有當初和其他工人一起去告公司。當時全體員工96人,有56人選擇留在新公司,其中八九個有長期合同,L和其他人都是臨時合同。公司也沒有通知這28人能否續約,職代會亦無回應。其餘40名工人對公司提起訴訟。這些經過鬥爭的工人,待遇都恢復到原來水準。
當時在做選擇之前,他曾向工會諮詢。工會說:“你們還是簽字吧,這樣比較好”;“現在公司的效益不佳,你們就離開公司吧。”職代會的表態也是一樣,總之是勸誘他們簽字離職。這些外籍工人第一次聽說公司“經營不善”,對這個陌生的詞搞不懂什麼意思,聽工會和職代會的人這麼說,便相信這個錯誤的意見。到了簽字之後,工人才得到消息,知道公司一早打定了主意要裁員,並且特地選了一些人解雇,這跟經濟危機沒有關係。他有23年工齡,但有的在公司才做了3年的人都保住了工作。今年底合同到期之後,不管能不能續約,他都下定決心要把公司告上法庭,爭取得到原先的工資水準和福利保障。
這裡,根據網上查到的資料做一點補充介紹。
德司達(DyStar)是全球最大的染料、紡織助劑及相關服務的供應商,原先有三家大股東——拜耳、郝斯特和巴斯夫,2004年為美國投資公司Platinum Equity收購。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後,德司達德國公司因“流動性不足”於2009年9月28日申請破產保護,11月底宣佈遣散屬下的法蘭克福、萊沃庫森等地工廠的員工。2010年2月新加坡KIRI公司收購其美國之外的全球業務,4月起“德司達的盈利能力已經恢復,全球業務逐漸步入正軌”。新加坡KIRI公司是印度KIRI染料公司為收購德司達而專門成立的控股公司,而中國的浙江龍盛公司持有印度KIRI公司7.46%的股份。據業內報導稱:收購德司達“真正的幕後導演或是浙江龍盛”。
土耳其裔工人L和S
土耳其裔工人S的介紹
S也是土耳其裔工人,在T公司做了13年(該公司與拜耳無關)。他講述的經歷和L很相似。全廠有600名員工(現在是500名)。後來公司說經營狀況不佳,要破產,解雇3個車間裡的140名工人。其中42人不接受公司的條件,不簽離職書(因此仍是公司員工,雖然被公司“自動解雇”了)。作為生產線上的員工,在公司宣稱破產之前,他們一直在整夜加班,因此每天都能感覺到,公司事實上收到很多訂單,解雇是資方降低用工成本的陰謀。他們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對資方提起訴訟。小組裡各種國籍的工人都有:土耳其人、德國人、斯里蘭卡、波蘭人,等等。他們搞遊行示威,利用媒體擴大影響。大家每兩周在科隆聚會一次,彼此團結,相互支持。他們相信只要堅持,必定會得到勝利。從今年(2010年)4月開始,工人陸續複職。小組鬥爭了一年之後,42人終於全部複職,也恢復了原來的工資。這場鬥爭完全是自發的,沒有依靠工會和職代會。工人當中,有的有孩子,有的買了房子要還貸。大家都害怕失去工作,但都團結並堅持鬥爭下去。鬥爭期間,他們沒有工資,靠失業金過活。複職後他們拿到欠薪,把失業金還給勞動局了。
S談到早先公司解雇他的詳情。當時他(還有他的鄰居)臥病在家休息,收到公司的通知,叫他不用上班了。職代會和他的師傅給他打電話叫他去公司,說有要緊事。他答說自己生病,不能去。他們就說:那我們去你家找你吧。S說,他從來沒有受到如此這般的重視。最後一個電話是公司人事部門打給他的,要他來公司。他問是什麼事。人事部門表示要跟他談。他打電話叫上工友一起去公司,人事部門接待了他,要他簽一份合同,同時假惺惺表示同情,要他在一天半的時間裡必須簽字。他反問道:“為什麼要簽字?”這份厚達13頁的合同的實質內容是:同意解除原來的勞動合同。合同上全是法律術語,S看不懂,於是要求公司給他一份影本:“我要徵求一下律師的意見,他讓簽的話我就簽。”說完這句話,他發現對方的臉色變了,顯得很緊張,但還是複印了一份給他。離開時,他聽到人事部的人在背後說:“你是個傻子!”他回敬道:“我會告訴你到底誰是傻子。”
出來後,他對等在門口的同事說:“現在我去找律師。我們拿到的是不公平的合同。我會告到德國政府去,政府不幫忙的話,就告到歐盟……如果你們願意跟我走這條路,就一起走。不願意的話我就一個人去。我們可是在民主社會……”
他把兩份檔交給律師:一份是公司解除合同的通知,另一份是通知他不用上班。律師看了之後,笑說:你勝訴的概率只有30%。一同前去的5名工友決定團結起來跟公司抗爭。他們還需要更多同事的團結和支持。可惜最後只有42人團結起來。他們搞過13次遊行示威,每次工人們都帶上家人,主要在萊沃庫森,兩次在杜爾塞多夫。這42人團結起來真是不容易啊。晚上,常有工友打電話給他,邊講邊哭:“我們能贏嗎?”他常常鼓勵和安慰對方。現在,他們都贏了。
講到遊行,S說,以前自己上班時,看到有人遊行,心裡會想:“這些人吃飽了沒事幹才去遊行。”到了自己遇上這樣的事,他才想到自己也可以這麼做:“遊行是個好辦法啊。”在德國,遊行的權利是有法律保障的。
報紙對T公司42名工人遊行示威的報導
他們的行動,得到一些組織的支援。
據介紹,德國的裁員需考慮人道因素,如果你有家庭、有孩子,或者孩子較多,都可計分,達到74分以上就比較安全。這42名工人多在75人以上。如果公司以經營不善為由裁員的話,工人去告資方,通常不會勝訴。2008年經濟危機後,德國很多企業都以此為由申請破產裁員。但S和工友們從不相信公司經營不善的托詞。因為公司只裁車間員工,很少裁文職管理人員。他們的官司是30年來唯一打贏的一場官司。最初他們要打集體官司,但德國法律只許以個人名義提起這類訴訟,所以後來分成42個單獨的案件。不管誰的案件開庭,其他工友都去支持,每次都一起出現在法庭上,連法官也被感動了,對他們表示同情。至於工人勝訴的原因,很難回答。法官的決定有可能受到輿論、工友團結等等的壓力和影響。
複職之前,S不是職代會成員。複職後,他和另一個參與過抗爭的工人加入職代會。職代會裡共有11名成員,另有5人和他們站在了一起。因此現在的職代會跟以前不一樣了。原來的職代會只代表資方,並不站在工人立場上,從未給工人辦過事。工人遇到問題找他們,職代會總是說:有工資就不錯了,回去工作吧。在他們抗爭之前,職代會沒有給工人以資訊或其它方面的支援,給工人的答覆是“我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今年S的計畫是要求公司取消派遣工制度:“我們需要勞務派遣工跟我們享有同樣待遇”。公司裡有21個勞務派遣工。這種做法已有15年的歷史了。派遣工通常都在正式工渡假時派上用場,工人渡假結束時,派遣工就少一些。前十年,派遣工和公司直接簽合同,近五年則是和仲介公司簽合同。
在這次鬥爭後,他還加入了工會。在他工作的13年間,只交過三個月會費,就退出了。
L和S的兩個案例令我們這些來訪者大感興趣。一方面,他們是兩個普通的底層工人,而我們都很希望能夠在德國之行中多接觸到底層的、一線的工人,更具體地瞭解德國工人的真實狀況,以及他們的困境。另一方面,不管國情怎樣不同,這類案例對中國勞工服務者來說也是接觸甚多,而易於引起共鳴的。大家一致認為,雖然S看起來覺悟更高些,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對資方的不信任,並團結其他工友一起對抗資方,但L的鬥爭性和堅定性更不可小視。因為S從自己受騙的經歷中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資方的欺詐,理解工人鬥爭的重要,從而在覺悟上產生一個飛躍。
“相互作用”計畫
關於這個機構。德方提供的資料中介紹道:
“‘相互作用’萊沃庫森俱樂部”這個計畫為社會各界人士提供互相碰面、交流和合作統籌的機會。“相互作用”為以下的人士提供碰面的機會:
• 失業者和被邊緣化的人
• 正規的從業人員
• 工作不穩定和沒有受到保障的從業人員
Y為我們介紹道,為了成立這個團體,他們準備了三四年。在德國,成立組織不用到政府登記註冊。不過,1年前他們在法院做了登記,這樣在接受捐贈之類的事情上有一些便利。
之所以起這個名字,是為了避免學校那種填鴨式教育。他們支援其它自發成立的小組織。參與到這裡來的個體與組織都必須有自己的主張,不能盲從他人的想法,並且要把小組發現的問題公開化、社會化。一項重要原則是:讓他們自己把自己組織起來的,不能讓前來參加活動的人完全依靠這個組織。核心思想包括:1、你可從中得到幫助,同時也付出你的貢獻;2、誰有好主意,大家一起商量來實現;3、最重要的就是空間,不只是地點和物理意義上的空間,也是想像的空間。在這裡,要找到一個大家可以聚會和分享的地方,並不容易。
失業是當今德國社會的重大問題。失業者是他們主要的服務物件。機構裡事實上有兩個組織,一個為失業者提供諮詢。負責諮詢的有2人,其中1個就是失業者,另1個是長期工作人員,本來在教會做,退休後教會取消了這個職位,他就來了這裡。從整個社會來看,這事情還沒什麼人來做。政府機構只管法律解釋,教會機構會去分析案例,但直接幫助受害者及提供諮詢的,就只有他們這類機構了(機構可以此為由向政府申請撥款)。機構裡的另一個組織從事“共同購買”,即以批發價買進食品一起分享,以減輕生活費用。機構還為失業者提供早餐。如果失業者跟勞動局的交涉出了問題,機構就陪同他們去勞動局解決問題。遊覽當地時,我們路過社區裡為失業者服務的救濟機構,其服務專案之一是到超市里廉價採購過期或即將過期、但仍能食用的食品,提供給貧困的失業者。
機構的場地後面有三個停車位,可供失業者搞自行車修車廠之類。
他們也為在職但感到沒有保障的工人提供諮詢,比如沒有合法居留證件的外籍工人。這些人來德國多年也得不到保障。他們通常只能找服務員之類的邊緣工作。這方面他們和威爾第(Ver.di)工會合作,為無證件人士提供援助。Ver.di是服務業工會,但得不到很多工會支持。所以還需要通過其它的行業工會向工會發出一些信號。他們希望建立一個人際關係網路,網羅醫生、律師等專業人士,以便給一些負債累累的人提供各種諮詢等。某些案例的情況很複雜,他們無法提供幫助,就可以轉送到較易為當事人信任的地方,比如律師那裡。
職代會是他們關注的一個重點。機構的作用就包括批評職代會。拜耳公司特別大,職代會不能事事處理。他們便成立小組,搞些遊戲什麼的,算是豐富工人的業餘文化生活吧。工人有一些問題沒法在工作中談,只能在工作後到這裡一起談。
Y說,對職代會,他們是很不滿意的,那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專制機構,對工人來說起不到作用。工會同樣傾向于資方。Y對他所接觸到的工會的工作方式都不滿意,同時他又認為這兩者都很重要。他本人是工會成員,但認為自己對工會沒有發言權,倒是想談一談職代會。他說,職代會的變化要從內部產生,也就是必須到職代會內部去做工作。就像波鴻歐寶汽車廠工會內的反對派(GOG,“反擊無極限”組織)一樣,他屬於職代會裡的反對派小組,他不想成為站在一旁的抱怨者。
工人如果對工會、職代會不滿,能夠怎麼做呢?當然,理論上,工人有選舉工會幹部的權利,因此假如不滿,工人在選舉時會有所舉動。但大家並不清楚在選舉時該怎麼做,而重要的問題不在於參加選舉的人,而是在於不去參加選舉的人。也就是說,半數工人對選舉不感興趣,不去投票。很明顯,這是大家對工會、職代會這些機構本身沒有信心的緣故。
在拜耳,只有20~25%的工人是工會成員。而按照法律規定,只有工會有權進行勞資談判。所以,儘管很多工人對工會不滿,但仍然留在工會裡。
拜耳工人Z的介紹
Z也是土耳其裔,在德國已經生活了36年。明年9月,他在拜耳的工齡就達到30年了。他受雇于德司達(Dystar)公司的化工部,曾是職代會成員,也是工會信任人,加入過化工業工會,但現在已成了反對派。Z給我們談起10月前拜耳工人的鬥爭。他的手頭有一個大資料夾,全是有關這起鬥爭的資料。當時公司提出與21名工人解除合同,條件是6個月停職留薪(等於放6個月的有薪假),之後不用來上班,資方給補償。但這些都成了空口承諾,就在他們應得到補償的前兩天,公司宣佈經營不善破產。Z覺得這太不公平了!他主動聯繫其他 20個工人,儘管不認識他們(因為工廠太大,他們也不住在萊沃庫森)。他也聯繫了“相互作用”組織,儘管並未奢望能得到多大幫助。
“相互作用”組織鼓勵他們鬥爭,願意並切實提供了許多幫助,例如解決會面地點,到宗教機構諮詢,與工會、職代會通話(這兩者沒有給予21名工人任何幫助),與媒體建立聯繫以便及時把他們的鬥爭情況訴諸輿論等。他們建議工人們組織一次示威,讓當地居民和拜耳區的工人都知道這件事。的確,再沒有其它組織説明這21名工人,連老天在內——遊行示威定在11月份,那天的天氣實在很惡劣。他們就大打廣告,對媒體說會有數千人參加示威。媒體來了以後才發現只有幾百人。那天前來採訪的媒體很多,包括德國、土耳其等國的大媒體都來了。消息播出的當天,土耳其裔工人的很多親朋好友打電話來,說在電視上看到他們了。
幾個月後,公司換了個名字繼續經營(這說明並非“經營不善”)。其餘的工人在“相互作用”組織的説明下到法院控告新公司。上個月(即9月份),法院告知Z,說他的案件已勝訴,可以複職。部分工人收到了賠償金。有的工人拒絕公司的補償,要求複職,今天也收到了複職通知。另有3人的訴訟尚未完結。
三個工人的案例都是關乎反解雇鬥爭的。可以說,這反映了德國以至歐洲多數發達國家工人們普遍面對的問題。莫非身處世界500強前列的拜耳集團缺乏“核心技術”或“自己的品牌”,沒有大搞“產業升級”,以致于無力為工人提供較好較穩定的工作崗位和工資福利?笑話!身為化工和製藥行業巨頭的拜耳擁有18萬項專利,6萬多項注冊商標。在戰後的大繁榮終告結束,資本主義再次深陷危機泥潭之後,資產階級力圖以自己的方式來解決資本積累的障礙,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於是起而取代了凱恩斯主義和社民主義,並席捲全球。裁員、減薪、消減福利才是當今資本主義世界的普世價值。昔日的勞資調和機構越來越猙獰地暴露出它們作為資方走狗的本色……
[1] 拜耳公司在大陸譯名為“拜耳”,萊沃庫森譯為“勒沃庫森”。
[2] 珍·艾弗思《公害大輸出》(臺灣,人間出版社1987年版,p56)
[3] 又譯“戴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