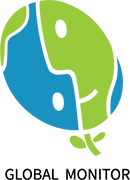來源:大河網 2010年04月26日
當紅潮在曼谷街頭洶湧,遊行、鮮血、槍殺、對峙、和談等等關鍵字貫穿著已經持續近兩月的紅衫軍示威行動,這一幕幕仿佛回到了1970年代泰國政治的場景,只是主角不再是學生和軍警,而是愈益壯大的公民社會和僵化未變的保守政治。
一般不瞭解泰國政治的人都會疑惑,幾年前才有黃衫軍的熱鬧,推翻了他信政權,怎麼紅衫軍又異軍突起,打著反獨裁的旗幟要求阿皮實政府下臺?若細究紅衫軍的 起源和發展,其中來龍去脈恐怕許多資深泰國問題專家也未必完全清楚。而事實上,紅衫軍的發展幾乎可以見證過去半個世紀泰國政治的歷史:從冷戰到後冷戰,泰 國共產黨的興起和衰落,以及公民社會的興起。
40年多前冷戰正酣的1973年,是泰國政治的分水嶺,也是今天紅衫軍的歷史起點。這一年,受越戰和歐洲“五月風暴”學運影響成立於1968年的泰國學生 組織“全泰學生中心”(NSCT)發動了反對軍政府獨裁的運動,史稱“10.14”運動,他儂-巴博政治集團倒臺,結束了1932年以來的泰國軍政府曆 史,也開啟了泰國公民社會之門,各類公民社會組織應運而生,奠定了今天泰國欣欣向榮的公民社會和社會運動基礎。在2006年發動推翻他信政權的黃衫軍,以 曼谷中產階級為主,就是這一歷史性轉折的結果之一。
但是,社會和歷史的分叉也同時發生。1973年之後泰國國王親自介入產生的1974年修憲雖然擴大了民選議員比例,但也招致保守政治勢力的反撲,特別是因 為冷戰局勢的變化,幾乎葬送了這一早於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革命——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始於1974年葡萄牙的民主化改革——而遲至1992年才重新啟動民主 化。但是,到1976年政變前,這一短暫的民主卻分別造就了今天黃衫軍和紅衫軍的基礎。
一支分叉,出於遏制雙方共同對手蘇聯-越南聯盟在印度支那的勢力擴張,1975年泰國和中國建交,一直相對對弱小、受外部支持的泰共獲得迅猛發展。而此時 的泰國民主政壇缺乏一個多數政黨,局勢日趨微妙之際,泰國軍方發動政變,並在1976年10月6-7日殘酷鎮壓了法政大學左翼學生的抗爭行動,導致100 多人死亡,3000多人被捕,稍後幾月的大逮捕行動更有多達8000多人入獄。
法政大學是泰國的精英大學,泰國政界、官僚以及商界的精英大部來自這間大學,但在1970年代的風潮下,左翼學生也是這間大學的主流。軍方殘酷鎮壓的結 果,中止了三年的民主化,也迫使大批左翼學生逃向泰北的叢林。隨後的一年裡,有3000多左翼學生和知識份子加入了泰共,泰國社會黨也宣佈與泰共合併。在 接下來的幾年,這些從法政大學屠殺中逃脫出來的泰國年輕學生們加入了泰共和泰國人民解放軍的訓練營地,但因不適叢林生活,而被以5到10人一組的方式派到 泰國北部和東北部的鄉村,尤其是長期隔離于泰國主體民族和主流社會之外的東北伊善地區農民就此開始動員、覺醒。
另一分叉,受北部農民運動的影響,泰國政府從1975年開始“撥款計畫”,第一次在農村將“農村建設計畫”納入財政撥款,主要在中南部鄉村進行基礎設施建 設。而1976年法政大學屠殺之後的泰國軍政府,當看到泰共和泰國人民解放軍的壯大,也嘗試向溫和的社會運動開放空間,允許甚至鼓勵1970年代初期建立 的公民社會組織更多地參與扶貧和社會公益事業。泰國的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紛紛加入其中,並新建了大批的非政府組織,特別是環境保護組織。整個1980年代 的泰國,一個溫和的公民社會雛形在威權政體之內蓬勃發展。
而冷戰形勢再一次的劇烈變化,造成泰共無可避免的衰落和失敗。1980年代初期,泰共獲得的外援支持減弱,越南-老撾政府驅離泰共在老撾境內的營地,叢林 中的知識份子們被迫走出叢林,放棄共產主義,回歸泰國主流社會。他們當中的不少人選擇加入如火如荼的非政府組織,繼續從事社運工作。二、三十年後,他們當 中的理想主義者成為今天泰國社會運動的主力,也開創了泰國政治的新版圖。只是,進入21世紀後,這批運動精英仍然被分裂的社會所分裂:他們分別介入反對他 信和支持他信的兩派鬥爭力量。
而整個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繁榮一度掩蓋了金錢政治、腐敗、和自私的利益集團精英們對民主的譛取。直到1992年5月兵變之後,政治改革被重 新提上公眾議程,政治改革成為知識精英和經濟繁榮下所孕育的新中產階級的呼聲。他們的主張不僅包括憲法修改,而且明確要求改革名不符實的選舉制度、進行教 育、官僚、福利和醫療的全方位改革,愈益激烈的政改爭論甚至涉及軍隊和國王體制。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後,這一爭論達到高潮,全面政改幾乎成為泰國的全 民運動,受金融危機影響而失業的城市勞工把政改的主張帶回農村,也激發了廣大農民的政治熱情。
然而,90年代更為顯著的政治變化卻來自農村:在泰國鄉村的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和動員。儘管直到今天,泰國城市尤其是中產階級主體的非政府組織更具影響,鄉 村地區的非政府組織還相當之弱,但是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農村已經廣泛建立各種形式的合作社,農村地區的自我組織以及與地方議員的聯繫都空前緊密。以 “泰國農村發展全國協調委員會”為例,其下已有兩百家NGO會員。關注環保、扶貧、醫療和婦女的各類組織在泰國鄉村不懈耕耘,雖然半數NGO都與環保有 關,環保卻是個更容易進入、更易被接受的領域,連不少泰國鄉間的佛教僧侶也參與其中,改變了許多農村民眾的參與意識,十幾年來已經悄然改變了鄉村的政治生 態。
動員的結果,首先是泰國鄉村婦女的覺醒。她們原本享有泰國傳統社會對婦女的尊重,卻是主流政治之外沉默的大多數,泰國婦女在議會、高級官僚和地方政客中的 數量和比例極低。廣大非政府組織在鄉村地區的參與和組織,則充分依靠和利用了婦女,她們則轉而成為改變農村社會經濟生活的主導力量。在Voravidh地 區的勞工運動中,在Maneerat的貧民窟鬥爭中,在Nalini的鄉村抗議中,在Naruemon的憲法行動中,婦女都是其中的主要推動者和參與者。 她們的參與不僅改變了泰國政治傳統中對婦女的極端偏見,而且,婦女們的參與和社會運動的力量一道推動著泰國農村自身重新認識被精英政治所忽略的聲音和訴 求。
在2000年召開的“伊善地區小農大會”和“貧困大會”上,來自泰國東北部的農民代表發出聲音,要求建設獨立於國家之外的公民社會,要求加強自組織能力的 培養。公民社會不僅僅是泰國城市中產階級的專利,也已經成為泰國廣大鄉村地區的願景和努力。對泰國非政府組織社工的調查表明,儘管第一代社工主要為受過良 好教育的城市中產階級,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NGO社工已經來自草根社會。
更具現實意義的,各種類型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和社會運動的興起,也説明了泰國鄉村地區的民主啟蒙和政治動員。2001年1月,亞洲金融風暴過後三年,在他信 領導的泰愛泰黨民粹主義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喚起下,泰國鄉村地區選民的投票熱情空前高漲,最終,泰愛泰党贏得248張下院議席,擊敗民主黨。占泰國人口五 分之四的農民的社會運動在民粹主義的快速動員下,與他信所代表的新興政治資本實現了聯合,泰國鄉村的聲音也第一次進入主流政治,泰國的全民選舉也由此真正 具備了民主的含義。在他信執政期間,他信在鄉村地區宣導的“30泰銖治百病”的醫保計畫贏得了廣泛支持。
在富有鬥爭傳統的泰國東北部(伊善)地區,這一發展尤其明顯,來自草根的社運成員,構成“紅衫軍”的基本群眾基礎,他們和懷抱1970年代政治理想的左派 知識份子一道加入紅衫軍的民主示威中。而與此相對,曼谷的中產階級以及工人階級卻站在敵視農民、擁戴王室的保守勢力一邊,他們組織的針對他信政權的黃衫軍 示威雖然最終取得了成功,卻也嚴重挫傷了人口占多數的農村選民。他信政府之後疲弱的阿皮實政府無力解決這一深刻的社會分裂和政治對抗,反而將這一矛盾指向 流亡海外的他信本人,不僅剝奪了他信政黨多數政客的參選資格,而且在今年2月授意法院剝奪他信私人財產,對他信的支持者來說意味著政治空間和政治名譽的雙 重壓縮與侮辱。紅衫軍再次走上街頭,幾乎是必然之勢。
目前,曠日持久且具耐心的紅衫軍似乎正贏得越來越多曼谷貧民的支持,也開始動搖軍營。面對來自貧困東北鄉村的紅衫軍,參與戒嚴的泰國軍隊士兵的心理正在發 生微妙變化,被敏感的泰國媒體評論為“西瓜兵”,也就是外表軍綠卻內心通紅。4月10日導致20人喪生的衝突和4月17日泰國警方抓捕紅衫軍領導的失敗之 後,和談成為各方唯一的解決方式。而無論何種和談結果,無論他信最終是否能夠回國,相信,都將意味著新一輪大選和紅衫軍的勝利,意味著街頭抗爭對殘留威權 下孱弱民主的救助。
(作者系清華大學政治學系講師)